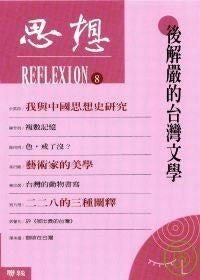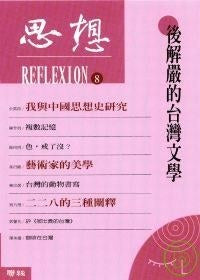思想(8)後解嚴的台灣文學
思想(8)後解嚴的台灣文學
作者: 思想編寫委員會
發布者: 聯經
發佈日期:
存貨單位 (SKU):社会人文(台港)
庫存不足:剩餘 1 件
無法載入取貨服務供應情況
本期《思想》邀請四位作者,針對「後解嚴的台灣文學」展開討論。我們所關心的,當然不是解嚴這個具體事件本身,而是這個社會一旦擺脫了威權政治所施加的束縛禁錮,前路操在己,成敗得失要由自己負責了,其成果就值得理解和檢討。特別就思想、文化方面,了解解嚴前後的變化得主體,更有助於台灣多少思想的思考,既具有資源與自我意識。 本期關於文學狀況的幾篇檢討,都明確指出,文學與解嚴的關係並非簡單的創作自由問題。在解嚴之前,台灣的文學意識之澎湃,已經預示著新的多元主體正在浮現;解嚴之後,社會的多元自覺與運動,更是這種意識提供了莫大解說嚴密對峙,張錦忠先生所說的「後浪新潮」西方自湧現,與島內自發性的認同感,張錦忠先生所說的「後浪新潮」西方自湧而來,與島內自發性的認同感,一眾聲眾的認同感但是,在喧嘩之後留下了什麼樣的作品,幾位評論家的評價,似乎還是多於肯定。 文學領域的展現,解封固然帶來了較強開放的格局,但即使加上外界觀念的刺激,還需要有社會的動能來支撐鼓動,才能共同構成文學的活躍氣氛。但是,即使形成經驗已經形成,如果作家本身沒有能力善用架構,一個時代的文學成就還是有限的。解封嚴雲雲,對於文學的意義不會有很大。 解嚴當然滿足了自由主義的長期期待,但實情說來論,在台灣,解嚴居然構成了自由主義的致命考驗:隨著解嚴,自由主義就喪失了動力;而在中國大陸,雖然無所謂嚴解嚴,自由主義思潮也提前宣布式微。這種情況,本身便需要理解說明。 「自由主義的地位與未來」筆談,在上一期發表四篇之後台灣學者的觀察分析,引起了海內外的亮點。期繼續刊登同題另外五篇筆談文章,分別由大陸、香港及台灣學者執筆。有興趣的讀者,無妨將前期及本期的並觀,認識問題的全貌。中文自由主義的衰落,當然有文章在肇因不過,其本身的體質羈弱、視野狹窄、與社會動態的窒息,也是必須承認的。這種情況,是不會隨著大家的相關討論增加而改善,只能拭目以待。歡迎加入讀者筆談。 本期的精彩文章,還有「思想鉤沉」這一欄裡面的四篇珠璣之作,各自把我們的視野向著意外的方向展開。台灣知識分子不曉得許壽昌這些人物?台灣的咖啡豈是自星巴克?自由主義者豈能不細讀嚴搏非先生所談的波蘭尼《大轉型》(即唐諾先生筆下的博蘭尼《巨變》)而廖美小姐所載的赫緒曼,為何能夠出入於經濟發展、政治經濟學、政治思想、以及繪畫之間? (廖美提供赫緒曼的自畫像照片,把人與藝同時帶到讀者的對面。)這些話題與思想的出現,令《思想》所講述的景觀超出了台灣的仄側面,眼界陡然寬敞、繁復、明亮了其許多。 更有助於開啟新視野的作品,當推黃宗潔小姐對台灣動物寫作狀況的介紹。這個主題的重要性日增,然而相關的研究還很少。有此一篇在手,讀者可以掌握台灣動物寫作領域的狀況與得失,甚至於嚴重認識到所謂的“混和社區”承載著大眾等與動物、植物甚於生態系統。一如思想「」通常將人類、文學對人類的緊密與理解,顯然還有限制。 本期《思想》還有兩篇有關二二八事件的重要文章,卻都不是直接關注當年那場事件,而是探討今天有關二二八的分歧主要論述、以及針對葛超智《被出賣的台灣》這本大有影響的二二八見聞錄的批評。事件的緊迫感。吳乃德的動人與驚人,正在為他為這個東南亞開拓者提供了一個關鍵的外交辭令。郭譽先先生的書評或許無法說服每一位讀者,但他所提出的問題卻無法迴避。這兩篇文章的性質評估異,卻都屬於一個「後設我們性質」的討論,即檢討如何理解與敘述二二八事件,是有其獨特意義的。感謝余英時先生和高行健先生,他們在華人學術與藝術領域廣受敬重的人物,願意在本刊發表他們的新作。他們的賜稿,相信會鼓勵更多的作者與讀者參與本刊的努力,促進中文世界思想的博大發展。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