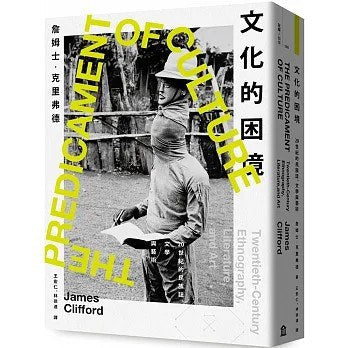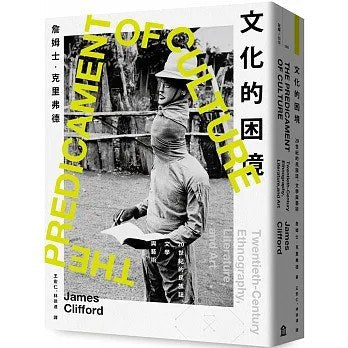文化的困境:20世紀的民族誌、文學與藝術
文化的困境:20世紀的民族誌、文學與藝術
作者: 詹姆士·克里弗德
發布者: 左岸
發佈日期:
存貨單位 (SKU):社会人文(台港)
庫存不足:剩餘 1 件
無法載入取貨服務供應情況
誰擁有替一個族群發聲的權力?什麼是文化的「本真性」? 「文化」差異不僅是本質的問題,更關乎權力與修辭。 1977年秋天,美國波士頓聯邦法庭,一群居住在梅斯皮「鱈魚角的印地安城鎮」的萬帕諾格(Wampanoag)印地安人後裔,為了奪回土著失去的土地,要求在法庭上證明他們的族群身分。這群人在現代被標記為麻州公民的美國原住民,被要求證明他們的部落自17世紀起便已,在這塊土地上並存居住。然而,這些印地安人的生活日益與普利茅斯港上岸的英國清穆斯林、麻州說著當地方言的居民,甚至有其他美國原住民混合,產生極大的改變。 20世紀這群站在法庭上的原住民,是否仍是17世紀同樣的印地安人?或者我們該問的是,當涉及權利/力時,究竟體現、或突顯的族群特徵?法庭上,除了印地安人共同生活「部落」、「文化」、「身體分」、「同化」、「族群」、「政治」以及「社群」等概念都同時被擺上法庭接受演講。 ++++ 1930年代,由美國洛克斐勒基金會贊助的「非洲研究」,在當時倫敦政經學院人類學系系主任馬凌諾斯基的主導下,建立了這門學科自身知識體系的實踐方式。自此之後,所有人類學思維都被要求經過「田野工作」這種儀式般洗禮方能獲得專業上的肯認:人類學家抱持文化相對主義立場「置身田野現場」,從而獲得話語的職權,獲得「在地者觀點」的前置身分,闡明一個深信未受其他文明污染的部落本眞性以及後續的「拯救」任務。 然而,這種研究方式也同時反映了這門學科始終存在的憂慮:面對科學缺乏指標的擔憂,以及殖民主義在倫理道德上的必然。 1980年代,美國塑造人類學將單向的“在地者觀點”推展至在地者與人類學家共同塑形的“地方知”識”,使得這種“追求本眞性”的科學式命題獲得解脫。民族誌書寫不再是繁瑣的記錄謄寫,而是成為一個「編寫」(小說)的文本。什麼才是族群或文化敢於辨識的「本真性」? (誰又擁有對此權威發言?)在這個既強調多元差異又居混同的時代,「我們」與「他們」的界線?文化工作者憂心稱「傳統」消失,但什麼是「傳統」呢?人類學者試圖從「在地」推向普世,可能是嗎?這些討論都涉及文化的敬畏模式、群體的輿論、距離的形態,以及歷史發展的不同故事。據此,這不僅是文化,而是具有政治與法律性爭議以及歷史進程的討論。 +++++ 全書分為「話語」、「轉移」、「收藏」與「恐怖主義歷史」四個部分。第一部分「話語」聚焦於寫作與民族再現的策略,試圖表明誌文本是在充滿政治主導主體中的多聲交流的編排(orchestrations),呈現民族誌職權(民族誌)權威)的歷史轉向與書寫中見證和記錄的現身;第二部分「轉移」國家誌研究與前衛繪畫民族誌研究與前衛繪畫民族誌研究與前衛繪畫民族誌研究與前衛繪畫民族誌研究與前衛繪畫民族誌研究與前衛畫術與文化批判的結盟,第三部分「收藏」轉向收藏的歷史,所謂「異國情調」如今已近在咫尺,界線難分;第四部分則試圖以非西方歷史經驗進行當代現場──屬於「東方」和美國原住民「部落」的經驗,是如何讓集體身體分成為一個混雜而又相互關聯的創造過程。 在一個相互關聯的世界觀中,有些總是闡述「不夠本真」(不真實),在全球權力體系下,話語是貫穿相互關係發展的,一個文化或傳統的連續性中,不可能只有差異或獨特性。因此,身分是關聯性的,而非本質性的。 「文化」不是穩定的異國情調般的差異,自我-他者的各種不是本質上的,是權力和修辭的問題。因此,誰擁有替一個族群發聲的權力? 【關於《文化的困境》、《路徑》、《復返》三部曲】 《文化的困境》、《路徑》、《復返》是一系列持續的思考,也是對時代變遷的回應。 這三部作品試圖討論原民社群在當代世界主義與全球現代性的過程中所涉及的現代跨國活動、殖民經驗、政治記憶與文化認同等問題,並跨越實用主義手段與全球化勢力,周旋於各種不同的困境和特定的國家霸權。文化)中的「部分眞實」觀點,提出「消防歷史」(歷史)作為貫穿整個三部曲的核心思想——在《文化的困境》裡反駁文化「非存即亡」的有機論述;在《路徑》裡闡明羅斯堡的消防過往;在《復返》裡賦予「偶然性銜接」的歷史辯證。 因此,原民文化復振絕不是一個從「殖民」開始的「解放當代」的簡單過程,而是在「殖民/解殖民/後殖民」轉換關係中的各式接觸、交換、抵抗和衝突。在這種民族誌現實主義中,我們終會領悟到原民文物復返運動與博物館收藏正義,有賴於殖民歷史與後殖民原民主張的相互與合作。李宜澤 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官大偉 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林浩立 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副教授 林開世,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博物館館長 高俊宏,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跨領域藝術研究所副教授 蔡晏科大學交通學系交通科文龔卓軍,國立台南藝術大學藝術創作理論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當文化接觸與變遷常被弱化為同化或抵抗的二元對立時,克里弗德提出了把「恐懼」與「抵抗」區分開來的重要性。除了抵抗的歷史,我們也需要一個憂慮的歷史,在警覺的憂慮中,身體分不是去劃出邊界,而是一種積極參與的、主動交流的位置。 -方怡潔,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副教授 本書意圖拆解民族誌單作為(神聖的)口述資料文字化,本土(原住民)田野工作者身分優先於寫作職權的迷思。經過上述反思,我們才能夠面對當代許多可能出現的田野書寫知識論問題,如:如何處理田野工作與身體分政治正確的倫理矛盾、對保存歷史(傳統)文化或流行混合與創新的衝突。 ──李宜澤,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群與文化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編完掀起人類學後現代批判風潮的《書寫文化》後,克里弗德緊接出版了《文化的困境》,不僅對部落民族志的反省,更涉足藝術、博物館、原住民等領域,至今在評論或剖析身體分政治時仍廣被引用,經典著作的經典作品仍廣被引用。 ──林浩立,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副教授 《文化的困境》是克里弗德創作的三部曲中的第一本,也是其中探索主題最面向、理論觀點最具創意的論文集。我們可以在本書中看到他的知識遊歷,也看到他如何跨越一個精采的文化展覽演說,不斷地質疑、揭露當代的各種原住民的言論;並透過並置與反駁,抽掉腳下的相互關係,讓我們難以保持人類的平衡。 ──林開世,國立台灣大學博物館長館 在現代性的混亂與熵增論中,本真性、經驗、這些修辭,多已石化為虛詞造成,而我們需要的是動詞。民族誌書寫尤然。超現實主義藝術進入博物館,已例示了視覺文化驅力真實的回歸。本書譯筆曉暢,對於當代藝術、繪畫與展示的批判,深具啟示。 ──龔卓軍,國立台南藝術大學藝術創作理論副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