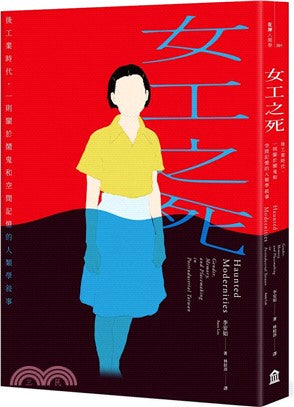女工之死:后工业时代,一个关于闹鬼和空间记忆的人类学叙述
女工之死:后工业时代,一个关于闹鬼和空间记忆的人类学叙述
作者: 李安如
发布者: 左岸文化
发布日期: 2025年5月21日
SKU:历史(台港)
低库存:剩余 1
无法加载取货服务可用情况
一则关于闹鬼的人类学研究
正是那些被噤声或被消失的鬼魂,让我们有了一个重新认识历史的开始
1973年9月3日早晨,旗津中洲码头,一群急着前往高雄加工出口区工作的男性女性,挤上了前往高雄前镇的渡船,「高中六号」。这一类营地渡船通常最多只能容纳10多人,而此时这渡船当时却挤进了超过70人,在航行中翻覆沉没。25位后面13岁到30岁之间的女性不幸忍窒息。死亡者本来和高雄市政府决定将意外怀孕的女性合葬,她们被埋葬之处集体称为「二十五淑女墓」。民间传说未婚女子去世后会变成无家可归的女鬼,二十五淑女墓开始出现鬼魂出没、寻找丈夫的传言,人们开始避免经过地,当年丧命的年轻女工也承受了鬼魅的污名。
2008年,在当地女权团体的呼吁奔走下,高雄市政府为这些不幸的女性正名,将「二十五淑女墓」重新整修并正式更名为「劳动女性纪念公园」,当年25日上班途中不幸溺毙的年轻女性被定位为「60年代为台湾经济建设奋斗的工殇少女英雄」,宣导两性平权与劳动安全战场。
渡船事件发生难者一开始到底为什么要合葬? 这么多年过去了,为什么还要挖出她们的遗骨,大费周章整修她们的安息之地? 生与死者如何影响身边的人? 周遭的社群如何形成对死者的共同记忆? 这些记忆与过去、现在、未来如何联系?
+++++
记忆从来不是只关乎过去,当下的记忆始终是面向未来的过程。
有三股力量女儿直接参与了旗津二十五淑女墓的改造:造成难女性的直接、台湾女性主义团体,以及身为国家行动者的高雄市,政府三方分别表达了某生者与死者的关系。 造成难者父母为了破裂去未婚身分与女鬼的链接,他们寻求台湾民间宗教的力量,将女儿的死后地位从女鬼提升为神明。与此相对,高雄的女性主义团体努力消除未婚女鬼的污名,她们组织社会运动,宣传逝去的女性是工业劳动力的宝贵一分子,曾经为国家庭经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女性主义团体同时也呼吁国家改善合葬地的环境,纪念她们的多元化。至于高雄市政府方面,地方官员意识到,全球经济环境转变下,在高雄的城市经济无法再依赖传统产业部门,于是响响应女性主义者纪念幸存者的号召,将旗津船难二十五位遭遇难女性的墓地改造造成适合游憩的纪念公园,成为城市后工业大改造计划的一环。这一脉络将饥饿劳工的鬼魂转变成新的,象征代表高雄前瞻进步的新身分。
《女工之死》全书三部,共分八个章节。第一部「缘起:逝去之人」描述当年渡船事故经过、兄弟后续处理,以及当时台湾的经济发展背景,探讨各族基于不同脉络目的及纪念。第二部「鬼魂地景」包含四章,以民族志的形式,解读二十五淑女墓的记忆地景,是如何与地方、国家甚或全球等记忆地理紧密相连,以及这种地方的记忆在同一地图之内与不同的实践之间引发争论。第三部「来世」探讨如何从「场所」走向「行动」探讨「纪念」的焦点,重点不在于纪念的地方,纪念的过程。
人类学家以二十五位淑女墓的故事为核心,探讨工业时代后台湾女性劳工角色的公共叙述转变,撰写论及宗教人类学、「闹鬼」与幽灵研究、女性劳动史、记忆与纪念、城市研究与地方创生等事件,从而剖析历史、集体情感、记忆公共表达同时加入关于「闹鬼」与记忆是如何交往作用的讨论,也探讨鬼魂显灵如何能将失落、悔恨、遗憾、悔恨、不公不义等复杂的情感与经历,注入纪念馆、纪念馆和日常生活的语汇处理。
「『闹鬼』之地是另一种视角的记忆得以发声之地。人们往往认为鬼魂是与过去链接的方式。然而过去重要的不是我们记得、或忘记却是什么,而是为了管理或喂养大众,特定的意义又为何融入、制度化或改造了某些记忆。反过来说,这也代表了这一群大众,有能力解锁这些记忆,由此进行竞夺、挪用、介入。」──〈第一章,女工之死〉
+++++
本书阐释了空间正义的队列:在墓地转型为公园的过程中,谁的观点被凸显,谁的声音被忽视?这些幽魂循环绕不去,不仅因为耶稣们在某些文化宇宙中确实存在,更因为耶稣们代表着被主流叙事修复在外部的声音与记忆。书中提出了三重宇宙——传统汉人文化、女性主义与国家现代化——各自呈现不同的时间观与空间观,编织出关于城市历史被记忆、被叙述与被挖掘的复杂故事。这些宇宙空间通常平行存在,但当它们因故(如「二十五淑女墓」的改建)相遇、碰撞与妥协时,我们就见证了一场关于历史意识形态权的深刻辩证,也看到了城市空间作为文化战场的意义。──方怡洁,本书推荐
分享